联系人:王老师
联系电话:19103817076
座机1: 0371-65350376
座机2:0371-65351916
父母面对障碍儿或情绪困扰孩童,又必须配合医学及心理检查测验,压力很大。因此,不论互动的状况如何,专业人员常被视为评论家,甚至是迫害者。深感焦虑、沮丧甚至怀有敌意的父母,经常以投射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情绪状态,而不是借由文字。面对投射的焦虑、敌意及沮丧,专业人员不免受到冲击,因此,想法有时会动摇,作出仓促的判断,例如:家庭中的某人或某事对其他人造成某种影响等。
一谈到自闭症,不可避免地就会问及它的病源。自闭症的起因并非本书之主题,但是这个议题极具冲击性,因为家长们一心一意想知道他们的孩子与他人不同的原因。自闭症的起因众说纷纭且两极化,对于全心协助孩童进展的父母而言,一味地探求病因可能会造成急性及慢性的痛苦。
与自闭儿家长合作时,专业人员容易将自闭儿对自身及家庭所造成的影响与病因混淆。尤其在20世纪40及50年代的美国,临床人员倾向于将与家属面谈的证据做为病因的诊断。他们没有考量到他们所观察到的现象可能是养育自闭儿后所造成的创伤之结果。而在塔非斯塔克中心,我们也从 未将父母的病理与自闭儿的关联等议题,作为研究自闭症的趋向。
在20世纪70年代,Tischler对于承继Kanner“冰箱母亲”理论所衍生的“父母应受谴责”言论,表示强烈反对。他提出了一套更精确、复杂的模式来说明仅仅只是责备父母亲是错误的。他也认为专业人员必须对探索病因的困难负责。对于研究、治疗或是母亲必须为被忽略的孩童的正常需求负责等议题,专业人员并没觉察自身的成见。他强调,专业人员总有情绪困扰的时候,包括过度认同受苦的孩童或父母,导致无意义的同情及谴责。部分专业人员对于“受苦”过于敏感,模糊了判断。他主张专业人员有必要了解自己,不致将自身的感受与家长的病理混为一谈;凡事避免仓促,尤其是在收集资料的时候。
Tischer的论点对于那些致力于提出诊断的专业人员而言,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与关联。从本章的主旨来看,他们必须思考清晰并提供最佳的治疗策略,有效地帮助家长来养育这些非典型的子女。因此,我建议专业人员必须要能够察觉并说出自身的成见以及我们的想法、介入意图、感受到的恐惧,以及脑海中的想像等,才不致于让这些因素过度阻碍我们对受创父母的理解及容忍。这种接受性的弹性需求也暗示了专业人员相互支持及训练的需求。
Tischler在1979年曾发表过《与精神疾患儿童共处:应用精神分析探讨精神疾患儿童家长之问题》。他在文章中深切地讨论父母怅然所失的量、质以及持续的时间,描述那种从生育到教养精神疾患儿童的挫折与紧张,导致慢性的“自我紧张”或“紧张性的创伤”。在父母的生活中,当专业人员试图介入并提供协助的时候,此类型的创伤会对专业人员造成某些冲击,而专业人员也会相继地造成对家长的冲击。
在我们介入评估或长期治疗前,某种模式早已建立。
Tischler写道:
我们在长期痛苦的结束及部分辞世后与家长会谈。他们的成人慢性重度创伤会因不同精神层次的个人或人际(包括婚姻)因素,而导致内在精神的反射以及适应过程。
简而言之,在与父母会谈之前,他们已经和孩子以疯狂的生活方式相处很久了。我同意Tischler的观点,对于他所描述的家有自闭儿的家庭,我也发现了十分类似的案例。自闭儿对于改变或不同事物所产生的恐惧,也可能变成父母的恐惧,或是呼应他们心中早已存在的惧怕。一旦他们已经养成不挑战或质疑现状的习惯,他们可能就会像自闭儿一样固执,因为害怕不好的结果,所以尽量避免任何大大小小的不愉快。整个家庭陷入相同的模式中,所有的事物都必须可预测后果或是一成不变,从而牺牲生活中自然发生的事件。寻求协助表示家长期望有些改变,当然也可能表示家长期望能够[FS:PAGE]治愈,对于发展过程毫无概念的人,他们会盼望奇迹式的完全改变。
在治疗的早期,父母在处理希望与失望起起落落的过程时是否产生困难,状况并不明显。在乐观的评估后重新燃起的希望却又痛苦得难以承受,毕竟希望只是希望,而非治愈。孩子若有进步,大家便欣喜若狂,也许在一周或一个月后,家长因为遭受些微挫折而深受打击,以致于无法认识到先前的进步。他们甚至会认为孩子的状况回到原点或是孩子产生退化现象;对他们而言,似乎只有好或坏而没有中间地带的比例、进步程度这回事。
家有自闭儿的父母因为试着努力去了解、鼓励和激发孩童而精疲力竭。有些人的反应是被牵绊、过度投入以及凡事介入掌控,以致于没有空间可言。有的人则是远离或是陷入悲伤的情绪。大多数的人则因为太多无法成眠的夜晚,孩子的大吵大闹,及缺乏限制及界线而疲惫不堪。他们失去了建立父母权威的意志,也失去了预测事情可能性的能力。他们觉得自己没效率,对孩子也不具有意义,因为孩子虽然需要他们,却从不表达任何的感激或情感。对孩子而言,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平时如何建立界线、限制及坚持,这些有用的资讯却无处可寻。
一般的父母会因为孩子而学习做个好父母,但自闭儿的父母则不然。寻求专业协助如同踩入地雷区一般,充满了被批判的恐惧,从一开始发现孩子不对劲,进而寻求诊断及协助,到专业的争辩等等不愉快的回忆再度被翻搅而起。
创伤及创伤后压力
Garland曾经描述了某些劫后余生者所经历的创伤后压力现象。若将她的想法与有自闭症相关诊断儿女的父母相串连,结果十分有趣。创伤后压力障碍可定义为超出常人经验之外的事件,并可能对大部分人造成巨大的痛苦。类似的事件包含了对儿女的威胁或伤害。可确定的是自闭儿的父母正遭受这种沉重又私人的灾难。每次与专业人员会面时,他们又必须把私人的悲剧痛苦地公开。我认为会在任何时间触痛他们的创伤的事件包括下列:
1、有关怀孕、生产或婴幼儿时期的创伤事件。
2、在家庭最无助时,造成家庭痛苦的非相关创伤事件。
3、在了解自己的孩子与他人不同的时候。
4、专业的诊断。
5、期待一个正常孩子的希望落空。
6、每天面对怪异或完全无法沟通的行为所产生的压力。
Garland认为当重度创伤启动,而存在于人格特性中的“错误线(fault lines)”延展开来时,便是遭受创伤后压力障碍的现象,因此,从未发展的病理过程便浮现。人们在无意识下任由创伤事件危险地入侵,这种侵入性的恐惧令人不由自主地想要逃避具提示性的事物。对某些父母而言,与儿女有关的创伤意味着孩子本身便是无意识的提示者。父母也自然地将与专业人员接触视为畏途,因为他们可能会唤起创伤。因此,提供详细病史或详记事件的能力严重受损。在接触与创伤相关的环境或事物时,紧绷的心理压力油然而生。在毫无预警下,专业人员的角色可能与在咨询时被触及的创伤相等。
创伤后压力障碍现象有其特殊的层面,一旦触及创伤,患者便会在原地踏步,重复地描述同样的情节。
我的患者父母中有一对夫妻,他们的儿子在八个月大时出现了自闭的征兆,他在出生后十天的时候患了感染性脑膜炎。只要他们出席,每周他们都会巨细靡遗地叙述儿子垂死的日子,以及医师所说的话,这种情况持续了一年。我的脑海里上映着一部惊悚的灾难/急诊室影片,久久无法消失。
诊断对父母而言是一大震惊,自闭症的诊断更是一大创伤。许多专业人员在告知父母诊断结果后却没有提供后续的支援,协助家长了解自闭症的内涵。有些专业人员谈及自闭状况的本质、孩童接受行为训练及特殊教育的需求、自闭症成人的机构安置或自闭状况的病理起源时,会低估他们的话所造成的冲击。
因此,自[FS:PAGE]闭症领域的专业人员有必要思考他们对家长造成的冲击,不尽是在诊断上,也在各种不同的早期咨询上。举例来说,错误的保证或过度的关切对于焦虑的父母会造成不好的影响。虽然他们的想法与专业人员相左,但是他们仍然盲目地听从。对于有意忽视现状的人,他们愿意相信嗜睡或被动的婴儿很正常,而且“长大就会好”。他们用心地观察到孩子缺乏社交互动、不会喃喃学语、单字期消失或以奇异的方式操弄玩具,于是寻求专业人员的协助,然而专业人员并不把这些状况当真,父母在违背自己正确的观察下听从专业的判断。家长总是为孩子的异常现象感到焦虑,当专业人员认为他们过度紧张或神经质时,有时又太轻易相信。
创伤会层层相叠。首先是注意到异常现象,然后寻求协助。接着是等待听取专业诊断。对某些人而言,可能还有与怀孕或生产、父母亲个人或大家庭有关之创伤。这种具毁灭性的私人悲剧足以动摇一个家庭的基石。
当父母将诊断的经验与专业人员会谈相连结时,心理治疗师很容易被视为一般的“专业人员”,同时,造成父母意识中的惊吓。当心理治疗师谈论诊断或病史时,他们就形同创伤。于是,他们可能被憎恨、遗弃,还要面对家长的缺席及明显痛切的敌意。
当父母在咨询室再度经历创伤时,也有可能让他们了解创伤的意义,并协助父母往前迈进。他们能够更实际,也能够更清楚地与孩子互动。这些考量有助于专业人员不要急于作出判断,能够与家长共同体验这种恐怖、痛苦的悲剧生活。创伤的希望工程能够激发专业人员自身的希望,对于要往前迈进、具支持能力且保持平衡比例的人而言是十分重要的。
父母的痛苦有时候会发泄在专业人员身上。受过心理动态训练者可以运用这种沮丧的情感转移来了解父母的状况以及未来的工作目标。换言之,专业人员会经历部分的创伤焦虑或恐惧,当父母的恐惧无处可去、无法处理时,它会弹回父母的身上,这是专业人员需要注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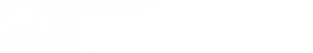
中方园校区:15981846548
共建合作咨询:19103817076(王老师)
地址:郑州市北环路中方园西区50号楼

Copyright© 2022 郑州市康达能力训练中心 豫ICP备11008710号 技术支持:郑州做网站-华久科技